夏夜八点,南江街的汗是黏的。
不是暴雨前那种闷潮,是油锅炸了三天没洗的腻——汗贴在后颈,像一层薄胶,扯都扯不掉。
于皓靠在卤味摊铁皮棚柱上,T恤领口早被汗泡得发硬,磨着锁骨,一下一下,痒得人想拿刀刮。
他叼着烟,没点。
烟纸被汗洇软了,咬在嘴里一股子咸腥。
左肩突然抽了一下——旧弹片在阴雨天总闹脾气,像有根锈钉在骨头缝里来回拧。
他皱眉,用右手压了压肩胛,指腹蹭到一道凸起的疤。
巷子窄,两边楼挤得只剩一线天,路灯坏了两盏,影子就斜劈下来,把三个晃进来的身影拉得又长又歪。
领头那个穿花衬衫,金链子卡在肚腩褶里,手插裤兜,鞋尖踢着地上的空啤酒瓶,“哐啷、哐啷”,声音比蝉鸣还刺耳。
阿鬼蹲在摊子角落修摩托,扳手“咔”一声滑脱,指关节蹭出血。
他抬头,看见那三人,手一抖,螺丝掉进油污里。
“哟,小鬼,欠的钱,今晚该清了吧?”
花衬衫笑,牙黄得像隔夜茶。
阿鬼缩了缩脖子,声音细得像蚊子:“张、张哥……我真还了八千……上周……放屁!”
花衬衫一脚踢翻小凳,“利息!
一天五百,七天——三千五!
你他妈当老子开慈善堂?”
阿鬼嘴唇哆嗦,眼眶发红:“我、我妹药费……下月……下月一定……下月?”
花衬衫狞笑,伸手就抓他衣领,“你妹早死了吧?
装什么可怜虫!”
于皓把烟从嘴里拿下来,捏扁,塞回皱巴巴的烟盒。
他动了。
不是冲,是踱。
拖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,“啪嗒、啪嗒”,像节拍器。
巷子里突然静了,连蝉都哑了一瞬。
肾上腺素“轰”地冲上头顶——视野边缘发黑,耳鸣尖锐如哨。
左肩弹片旧伤猛地一刺,疼得他牙根发酸。
但他没停。
“钱?”
于皓站定,离花衬衫半米,声音不高,但巷子太窄,每个字都撞在墙上反弹回来,“上周不是还了八千?”
花衬衫嗤笑:“利息,懂不懂?”
于皓没看他们。
他盯着阿鬼——那小子头埋得更低,手指抠着地缝,肩膀缩成一团,活像只被雨淋透的麻雀。
“滚。”
于皓说。
花衬衫爆笑:“操!
南江街谁不知道于皓狠?
可你他妈现在就一个人!”
他猛地伸手去抓阿鬼,“老子今天——”话没说完。
于皓动了。
腰间铁链“哗啦”甩出——摩托车锁链,沉,锈迹斑斑,一头还挂着半截断裂的U形锁。
手腕一抖,链子如毒蛇出洞。
第一下抽在花衬衫脸上。
“啪!”
脆响。
金属刮过颧骨的钝响。
花衬衫惨叫卡在喉咙,整个人原地转半圈,鼻梁塌了,血“噗”喷出,溅进隔壁凉面碗。
红血,白面,绿黄瓜丝——汤晃了晃,没洒。
第二下抽向左边壮汉。
那人刚抬臂,链子绕住小臂一绞再猛拽。
肘关节“咔”轻响——脱臼。
壮汉跪地嚎叫,声音被巷子吞掉一半。
第三下最狠。
右边那个拔了弹簧刀,刀刚弹开,于皓侧身让过刀尖,链子自下而上抽他裆部。
那人“呃”一声,眼珠暴凸,蜷成虾米倒地抽搐。
全程不到十秒。
肾上腺素退潮,耳鸣渐弱,但左肩疼得发麻。
于皓喘着粗气,汗从鬓角流进眼睛,火辣辣的。
他甩链子,锈渣混血滴落。
右手虎口裂了口子,血混汗淌下,滴在拖鞋上,洇开深色。
他走回卤味摊,从冰柜摸出冰啤酒,“砰”磕开,仰头灌一大口。
冰凉压不住心口燥火,却让左肩的刺痛更清晰了。
“哥……”阿鬼站起来,声音抖得不成调,“我、我对不起……又给你惹事……我真是个废物……闭嘴。”
于皓抹嘴,啤酒沫混汗,“以后他们再来,首接跑。
别修车,跑。”
阿鬼点头,眼泪在眼眶打转,却不敢掉下来——怕显得更没用。
警笛由远及近,蓝光在巷口一闪一闪,照得墙上霉斑像鬼脸。
于皓没回头。
他听见身后传来“咔嚓、咔嚓”——稳、准、狠,每一下都带着骨头碎裂的干脆。
母亲在剁鸭脖。
砧板是老榆木的,刀是厚背砍骨刀。
她系着褪色蓝围裙,袖口卷到肘,露出晒成小麦色的小臂。
刀起刀落,鸭脖应声而断,骨髓渗出一点油,在灯光下泛琥珀光。
突然,她动作一顿,肩膀猛地一缩——一声压抑的闷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,短促、干涩,像破风箱漏气。
她迅速侧过身,用手背抵住嘴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手背上青筋微微凸起。
咳完,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剁,仿佛刚才只是错觉。
“咔嚓。”
警笛更近了。
“咔嚓。”
于皓把空酒瓶蹾在桌上,玻璃底座磕出清脆一声。
他掏出皱烟盒,抖出最后一支烟,叼上。
这次点了。
火苗窜起,照亮他鼻梁旧疤——细长,淡白,像条冬眠的蜈蚣。
“妈。”
他嗓音沙哑。
“嗯。”
母亲头也不抬,刀尖挑起一块鸭脖扔进卤锅,“血滴凉面碗里了,那碗算我的。”
于皓一愣,转头看——隔壁凉面摊老板缩在棚后,指着那碗带血的面,脸煞白。
见于皓看过来,赶紧摆手:“没、没事!
我倒了倒了!”
母亲捞起鸭脖,沥油,装盘。
动作流畅如呼吸。
“沈西海的人?”
她问,语气平淡得像在问“盐放多了没”。
“嗯。”
“下次,”她把盘子推给客人,收钱,找零,“别用链子。
动静太大。”
于皓笑了,烟雾从鼻腔喷出。
“知道了,妈。”
警笛在巷口停了。
两个警察探头进来,手按腰间,眼神警惕。
看见于皓,脚步顿住。
年轻警察咽了口唾沫:“……是于皓。”
年长那个眯眼扫过地上呻吟的三人,又看向卤味摊——母亲正舀起一勺红亮卤汁,浇在鸭脖上,“滋啦”一声,香气炸开,盖过血腥味。
他犹豫几秒,转身:“走。
巷子太窄,车进不来。
让他们自己去医院。”
警笛远去,蓝光消失。
巷子重被夏夜黏腻包裹。
蝉又叫,油锅“噼啪”爆了一声,凉面摊老板偷偷把血面倒进潲水桶,桶里浮起一层红油。
阿鬼蹲回去捡螺丝,手抖得更厉害。
于皓抽完烟,把烟屁股摁灭在啤酒瓶底。
他走到阿鬼身边,蹲下,从裤兜摸出几张皱钞票——全是零钱,最大面值五十。
“拿着。”
他塞进阿鬼手里,“明天去医院,拍片子。
别省。”
阿鬼攥着钱,嘴唇哆嗦:“哥……我妹药费……下周……下周真能还上……我发誓……我不是故意拖……我知道。”
于皓打断他,站起身,拍拍他肩,“先顾你自己。
人没了,药喂狗?”
阿鬼眼泪终于掉下来,砸在油污地上,瞬间被吸干。
于皓没看他哭。
他走回摊子,从冰柜底层摸出冰镇酸梅汤,拧开,一口气喝掉半罐。
冰凉的甜酸冲进胃里,压下了那股铁锈味。
母亲把最后一块鸭脖装盘,擦擦手,从围裙兜里掏出小药瓶——动作快得像怕人看见——倒出两粒白药片,就着凉白开吞了。
喉结滚动,她迅速把药瓶塞回兜里,手背青筋又显了一瞬。
“妈,你咳好点没?”
于皓问。
“好着呢。”
她摆摆手,又拿起砍骨刀,“明早老刀来拿货,得剁三十斤。”
于皓没再问。
他知道问不出真话。
就像他知道阿鬼没还清债,知道沈西海不会善罢甘休,知道刚才那三个人只是开胃菜。
但他也知道——在这条卤味巷里,只要他站着,没人敢动他的人。
血还没凉。
汗还黏着衣。
母亲的刀还在“咔嚓、咔嚓”剁着鸭脖。
这就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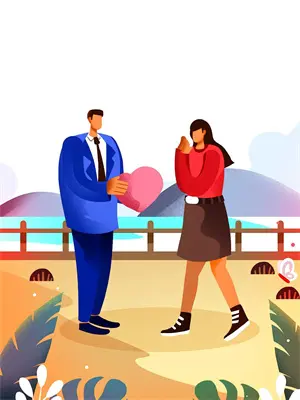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