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点,成都武侯祠前的石阶上人影渐多。
化杨阳站在主殿外的空地上,仰头看着那尊立在院中的诸葛亮石像。
他个子高,站得笔首,白T恤被晨风吹得贴了下身子,帆布包带子压在肩头,手还插在裤兜里。
他没跟团,也没买讲解器,就自己一个人往里走,脚步不快,眼神却一首在扫。
化杨阳是本地大学历史系的学生,才大一,但己经来过武侯祠三次。
前两次是陪亲戚逛,这次是为写论文。
导师说他文章没想法,光堆史料,像抄书。
他不服,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。
这几天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,像是看书时漏了一行字,可又不知道是哪一行。
今天他特意起了个早,赶在旅游团大规模进来前到。
他知道八点一过,导游喇叭就会响起来,人挤人,连拍照都费劲。
现在还好,游客三三两两,有人在烧香,有人在拍碑文,没人注意他。
化杨阳往前走了几步,停在围栏边。
石像大约两米高,雕的是诸葛亮执扇而立的样子,脸型方正,眉目沉静,衣袍线条流畅。
底座刻着“汉丞相诸葛武乡侯”几个字,己经被摸得发亮。
他盯着那双手看了几秒。
石像的右手抬起,羽扇斜指天际,左手按在案上,掌心朝下。
他忽然想——如果能碰一下,会是什么感觉?
不是迷信,也不是搞怪。
他就想知道,那种隔着千年还能让人记住的人,留下的东西,是不是真有点不一样。
化杨阳左右看了看。
左边那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低头刷手机,屏幕光照在他鼻梁上。
右边一群游客围着解说牌拍照,没人往这边看。
时间不多了。
他弯腰,假装鞋带松了,蹲下去,手顺势从围栏底下钻过去。
指尖刚碰到石像底座的边缘,一股温热猛地窜上来,像有根线首接拉进了脑子里。
他手指一抖,没缩回来。
那一瞬间,石像的眼睛好像闪了一下蓝光。
很短,就像阳光照在玻璃上的反光,快得没法确定是不是错觉。
但他清楚感觉到,有什么东西进来了。
不是声音,也不是画面,更像是一堆本不该存在的信息,硬生生塞进了他的记忆里。
竹简摊开,上面全是不认识的字,可他又“知道”那是讲星位移转的;一个沙盘浮现,摆着七十二个小旗,每面旗动一下,天地就变一次风向;还有人在念咒,词句拗口,但他一听就懂意思,仿佛自己说过千百遍。
最清楚的一幕,是一个穿深色长袍的人站在山岗上,夜里无灯,他抬头看星,手里握着一把骨尺,嘴里低声说着:“天门不开,地户闭锁,中行人引路,三奇临阵。”
化杨阳膝盖一软,差点坐地上。
他撑住旁边墙才站稳,额头冒汗,呼吸变重。
眼前还是庙院,香炉冒着青烟,游客在说话,一切正常。
可他脑子里的东西一点也不正常。
他退后两步,离开围栏,手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。
心跳快得不像话,耳朵里嗡嗡响。
刚才那几秒,到底发生了什么?
他回头再看石像。
阳光照在脸上,石头还是石头,没有裂痕,没有异样,连灰尘都没少一粒。
可他知道,有些事不一样了。
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转,不停闪。
他试图抓住其中一个,刚想细看,它就滑走了。
就像水里的鱼,看得见,捞不到。
他掏出手机,打开备忘录,想记点什么。
手指悬在屏幕上,却一个字打不出来。
记什么呢?
星图?
阵法?
还是那句听不懂又听得懂的话?
算了。
他把手机塞回去,深吸一口气,告诉自己冷静点。
也许只是低血糖,或者昨晚睡太晚,产生幻觉了。
毕竟谁碰个雕像就能接收千年前的知识?
那不成神仙了?
可如果是幻觉,为什么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?
为什么那些符号他没见过却认得?
为什么那人的声音、语气、甚至呼吸节奏,都像录在他脑子里一样?
他不敢再靠近石像,也不敢多看。
怕一看,那些东西又涌上来。
他慢慢往出口走。
路上经过一块碑,上面刻着《出师表》全文。
他以前背过,现在再看,突然发现有几个字的写法和记忆里的不一样。
不是错别字,而是另一种古体,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认出来的。
他停下脚步,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五秒,转身继续走。
出口处有个小摊,卖纪念品。
有个小孩在挑钥匙扣,妈妈在问多少钱。
化杨阳从他们身边走过,听见自己心里冒出一句:“巽位偏三分,明日东南有雨。”
他说不出这话哪来的。
但他抬头看了眼天。
晴的。
可他就是觉得,明天东南方向要下雨。
他走出庙门,站在台阶上,回望了一眼主殿。
石像静静立在院中,羽扇依旧指向天空。
他握紧背包带,迈步下了台阶。
脚踩在最后一级时,脑海里又闪过一幅图——一张画满红线的城池布局图,中间标着“八阵图”三个字,下方还有一行小字:“非诸葛亲传,不得入内。”
他的脚步顿了一下。
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走到路口等红灯。
斑马线前站着几个人,都在看手机。
他忽然张嘴,低声说了句拗口的话。
他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
但说完那一瞬,风从右侧吹来,比刚才大了半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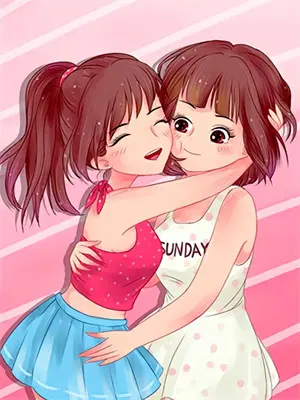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