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7月27日的铜城,被一场连绵的阴雨泡得发潮。
铅锌厂家属院外的土路积着水洼,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,连空气里都飘着股铁锈与潮湿混合的怪味。
赵卫国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,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那是六年前“88·5·26”案现场的照片,林晓燕的白球鞋在照片里泛着冷光,鞋尖的血渍像凝固的朱砂。
“赵队,刚接到报案,供电局宿舍那边出事了!”
年轻警员小李撞开值班室的门,雨衣上的水珠顺着裤脚往下淌,“有人在家遇害,场面……跟六年前那个案子有点像。”
赵卫国手里的照片“啪”地掉在桌上。
他猛地站起身,抓起椅背上的外套就往外冲,连雨衣都忘了穿。
警车在雨幕中疾驰,雨刷器疯狂地左右摆动,却始终刮不干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,就像他六年来始终抹不去的记忆——林建军通红的眼睛、受害者家属的哭声、现场那枚刻意留下的指纹,还有至今悬在档案柜最上层的“88·5·26”案卷宗,封面的“未破”两个字像根刺,扎得他心口发疼。
供电局宿舍在城市另一头,是栋比铅锌厂家属院更老旧的五层红砖楼。
警车刚停在楼下,就看见几个居民围着单元门口议论,有人捂着嘴小声哭,有人指着三楼的窗户不停摇头。
赵卫国踩着水洼往楼上跑,楼道里的声控灯被脚步声惊醒,昏黄的光线下,他看见三楼门口的地面上,有几滴暗红的血迹顺着楼梯缝隙往下渗。
“赵队,您来了!”
负责保护现场的民警迎上来,声音发颤,“受害者叫宋佳,十九岁,是供电局的实习生,一个人住在这里。
发现人是她的同事,来拿资料的时候看见门没关严,推门就……”赵卫国没等他说完,戴上手套和鞋套,轻轻推开虚掩的房门。
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,混杂着雨水的潮气,比六年前的现场更让人窒息。
客厅的沙发歪在一边,茶几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凉茶,杯壁还凝着水珠,旁边摊着一本翻开的《电力安全规程》,书页上溅着几滴血。
卧室的门敞开着,宋佳倒在床边的地毯上,浅蓝色的连衣裙被撕裂,露出的皮肤上布满深浅不一的创口。
她的头歪向一侧,眼睛还睁着,瞳孔里映着天花板的裂纹,颈部有一道整齐的切口,鲜血浸透了地毯,在身下积成一片深色的水渍。
“老刘,怎么样?”
赵卫国蹲在法医老刘身边,声音压得很低,怕惊扰了这个年轻的生命。
老刘正用镊子轻轻拨开宋佳颈边的头发,眉头拧成一个结:“颈部锐器切割伤,切断颈动脉和气管,是致命伤。
上身有三十六处创口,分布在胸、腹、肩部位,创口边缘整齐,和‘88·5·26’案一样,是单刃刀具造成的,刀刃长度估计在十五到十八厘米之间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用镊子夹起宋佳指甲缝里的纤维,“这里有蓝色棉麻纤维,跟林晓燕案里发现的,材质一模一样。”
赵卫国的心脏猛地一沉。
他抬起头,目光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:五斗柜的抽屉被拉开一半,里面的化妆品和零钱都在,排除抢劫杀人;窗户是从里面扣死的,窗台上没有攀爬痕迹,凶手还是从正门进入;门把手上,两枚清晰的指纹印在潮湿的木头上,右手食指和拇指,其他地方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——和六年前的手法,分毫不差。
“小王,提取门把手的指纹,立刻送回局里比对‘88·5·26’案的指纹档案。”
赵卫国站起身,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,“再仔细搜一遍房间,特别是床底、衣柜这些死角,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”
小王点头应下,拿出毛刷和银粉,小心翼翼地处理门把手的指纹。
赵卫国走到客厅,拿起茶几上的《电力安全规程》,书页停在“触电急救”那一页,旁边有宋佳用铅笔做的标记,字迹清秀。
他想起六年前林晓燕缝纫机上的《电工基础》,心里一阵发酸——两个同样年轻、同样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孩,却都倒在了凶手的刀下。
“赵队,宋佳的同事来了。”
小李在门口轻声说。
赵卫国放下书,走到门口。
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女人站在楼道里,脸上还挂着泪痕,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文件夹:“我是宋佳的师傅,叫刘梅。
今天下午两点,我让她帮我整理一份资料,说三点过来拿。
结果我三点到的时候,看见门没关严,喊她也没人应,推门进去就……”她说着,眼泪又掉了下来,“宋佳这孩子特别乖,刚从技校毕业,每天都提前半小时到单位,还主动帮同事打扫卫生,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!”
“你最后一次见宋佳是什么时候?”
赵卫国问,“她有没有跟你说过,最近有什么人跟踪她,或者遇到什么奇怪的事?”
刘梅擦了擦眼泪,仔细回忆着:“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,我们一起走的,她还跟我说,最近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她,特别是晚上加班回家的时候。
我还劝她,可能是她太紧张了,让她以后下班跟我一起走。
没想到……”她哽咽着说不下去,“今天早上她来上班的时候,还跟我笑着说,昨天买了件新裙子,等休息的时候穿给我看。”
赵卫国的心揪得更紧了。
凶手不仅手法没变,连选择目标的方式都一样——年轻、独居、可能被提前跟踪。
他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,雨水顺着窗沿往下流,打在楼下的梧桐树叶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远处的铁路线上,一列火车正缓缓驶过,鸣笛声在雨幕中显得格外沉闷。
“刘师傅,你知道宋佳有没有男朋友,或者经常来往的男性朋友?”
赵卫国问。
刘梅摇摇头:“没听说过。
她平时除了上班,就是回家看书,很少出去应酬。
她的父母都在外地,在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同事。”
这时,小王拿着指纹比对报告跑了进来,脸色苍白:“赵队,比对结果出来了!
门把手的指纹,和‘88·5·26’案现场提取的指纹,纹型、特征点完全一致!
是同一个人!”
赵卫国闭上眼睛,深吸了一口气。
六年了,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凶手,终于再次露出了踪迹。
他睁开眼,目光变得坚定:“小李,立刻通知局里,申请将‘94·7·27’案与‘88·5·26’案并案侦查,成立专案组,我要当组长。”
“是!”
小李立刻跑下楼打电话。
老刘站起身,拍了拍赵卫国的肩膀:“老赵,六年了,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
这次,我们一定能抓住他。”
赵卫国点点头,却没说话。
他知道,凶手敢在六年后再次作案,还沿用同样的手法,说明他不仅没有收敛,反而更加嚣张。
而且,从铅锌厂家属院到供电局宿舍,两个案发地相隔五公里,凶手的活动范围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大。
专案组很快成立,办公室就设在公安局的旧会议室里,墙上贴满了案件资料和现场照片。
局长把两本厚厚的卷宗拍在桌上,烟灰落在泛黄的纸页上:“同志们,这两起案子,是铜城刑侦史上的耻辱。
六年前,我们没能抓住凶手;六年后,他再次作案,这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挑衅!
从今天起,所有人取消休假,全力以赴,必须尽快破案!”
“是!”
会议室里的警员齐声应道,声音震得窗户玻璃微微发颤。
赵卫国站在地图前,用红笔在铅锌厂家属院和供电局宿舍的位置各画了一个圈:“根据两起案件的现场勘查和走访情况,我们可以确定,凶手是同一人,男性,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,身高1米7左右,中等身材,可能从事体力劳动,熟悉铜城的地理环境,有反侦察意识,并且可能对年轻独居女性有特殊的报复心理或变态癖好。”
他顿了顿,继续说:“另外,两起案件的受害者都在工厂或事业单位工作,凶手可能在这些单位工作过,或者有亲友在这些单位工作,方便他了解受害者的作息和生活习惯。
还有,受害者指甲缝里的蓝色棉麻纤维,很可能来自凶手的工作服,我们要重点排查全市所有使用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工厂和单位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里,专案组的警员们像上了发条的钟,连轴转。
他们走访了铅锌厂、供电局的所有职工,排查了城区有流氓劣迹的三百多人,调取了近五年的离职人员档案,甚至连周边县区的工厂都不放过。
小王带着技术人员,跑遍了全市所有销售单刃刀具的商店,登记了近千把符合特征的刀具,却始终没有找到与案件相关的线索。
赵卫国每天都泡在办公室里,对着卷宗和照片发呆,常常一看就是一夜。
他的眼睛布满血丝,下巴上冒出了胡茬,整个人瘦了一圈。
小李看他太累,劝他休息一会儿,他却摇摇头:“案子没破,我怎么睡得着?
宋佳的父母明天就到了,我怎么跟他们交代?”
这天晚上,赵卫国正在整理走访记录,小李突然跑了进来,手里拿着一份电报:“赵队,包头公安局发来的电报,说他们那边最近发生了两起命案,作案手法和我们这两起案子高度相似,受害者都是年轻独居女性,颈部有致命切割伤,现场也发现了蓝色棉麻纤维。”
赵卫国猛地站起来,抓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,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:“凶手在流窜作案!
他从铜城跑到了包头!”
他立刻拿起电话,拨通了包头公安局的号码,希望能获得更多线索。
然而,包头那边的调查也陷入了僵局。
凶手在包头作案后,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
赵卫国放下电话,看着窗外的雨,心里一阵无力。
六年的追查,好不容易有了新的进展,却又因为凶手的流窜,再次陷入了僵局。
他走到墙边,看着林晓燕和宋佳的照片,照片上的两个女孩笑得那么灿烂。
他伸出手,轻轻抚摸着照片,低声说:“放心,我不会放弃的,一定抓住凶手,还你们一个公道。”
雨还在下,敲打着窗户,发出“哒哒”的声响。
赵卫国重新坐回桌前,翻开卷宗,继续研究那些己经看了无数遍的线索。
他知道,这条路还很长,但他不会停下脚步,因为他是一名刑警,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宁,是他的责任。
而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凶手,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,落入法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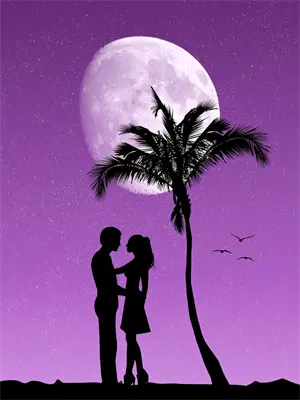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