次日清晨,寒风卷着枯叶在刑场边缘打旋。
天色灰白,云层低垂,像一场雪迟迟不肯落下。
死囚们被押到空地列队,跪在冻土上,铁链拖地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西周各堂口弟子围观,神情肃穆,无人说话——在金鸳盟,刑场不是看热闹的地方,而是震慑人心的祭坛。
许宴跪在地上,枷锁沉重,肩胛骨被磨出深痕,每次呼吸都牵动胸前未愈的鞭伤。
他低着头,目光却悄然扫过每一处细节。
柳七娘被绑在一根孤立的木桩上,位置比其他死囚更靠前,像是特意用来示众的。
她衣衫单薄,双手反绑在身后,指尖冻得发紫,裂口渗出血珠,染在麻绳上。
嘴唇干裂,仍在微弱地开合:“我没看见……我真的没看见……”那不是求饶,是辩白,是濒临崩溃也不肯认的倔强。
许宴心头一震。
他知道这女人为什么被抓——药堂杂役,因夜里误入禁地被指“窥探机密”。
但真正致命的是,她曾替人送过一碗安神汤到角丽谯密室外廊,那是几天前的事。
当时值夜的是刑堂弟子,而那晚之后,药方残页就不见了。
所有证据都指向她,可偏偏没人能证明她真的进了密室。
更巧的是,她被捕那晚风很大,地面干燥,如果有人潜行,脚印应该很浅。
可刑堂的记录却写:“泥地留有清晰足印两寸深,方向明确,系独自潜入。”
矛盾就在这里。
许宴闭了闭眼,想起牢墙上那些刻痕记录的天气。
昨夜狂风不止,沙尘漫天,如果她要逃,怎么会选这种天气?
而脚印深达两寸,除非她是拖着东西走,或是……被人拖着伪造痕迹。
一个念头刺入脑海:栽赃。
而且是刑堂内部的人做的。
可他现在说出来,谁会信?
申屠烈不会给他开口的机会,一旦被扣上“扰乱刑律”的罪名,别说任务,连命都保不住。
系统警告还在耳边——严禁泄露核心剧情。
他不能提未来,不能说派系斗争,更不能点破角丽谯与笛飞声的暗斗。
但他可以讲“梦”。
昨夜,他确实做了一个梦。
梦里黑雾弥漫,一条幽冥长河横在眼前,血水翻涌,无数冤魂哀嚎。
他被铁链拖到殿前,阎王端坐高台,面如青铜,目光穿透魂魄。
一声喝问:“尔阳寿未尽,因何而来?”
紧接着,画面涌入识海——柳七娘蜷在药房角落,颤抖着捧起一碗温热的汤;她脚步虚浮地走过回廊,鞋底沾尘却没有深痕;然后黑影出现,将她打晕,拖进风沙里……醒来时,冷汗浸透囚衣。
这不是预知,是系统给的提示。
协助化解一场冤案——任务目标明确,奖励诱人,但他必须用“合理方式”完成,不能暴露身份。
于是,他决定赌一把。
当申屠烈踏上刑台,黑袍翻飞,手中罪状卷轴缓缓展开,声音冷得像刀刮骨头:“柳七娘,私通外敌,窃取《九转还魂丹》残方,证据确凿。
今当斩首示众,以正纲纪!”
台下众人沉默低头,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就在这片死寂中,一道沙哑却清晰的声音划破空气——“且慢!
此女无罪——我知真相!”
全场骤然安静。
所有目光齐刷刷转向声音来处。
许宴缓缓抬头,脸颊瘦削苍白,眼中却燃着一簇冷火。
他跪在地上,身形佝偻,但脊梁挺得笔首,像一根不肯折断的竹子。
申屠烈眉头一拧,目光如刀射来:“你?
一个将死之人,也敢妄议刑案?”
许宴没有退缩。
他知道,这一刻稍有软弱,就是万劫不复。
他迎着对方杀意凛然的目光,声音平稳而坚定:“昨夜梦中,阎罗亲授因果——”话音未落,人群中己有嗤笑声响起,连远处观刑的执法弟子都不屑摇头。
荒谬!
竟用鬼神之说来挑战刑堂威严?
可许宴依旧稳稳跪着,仿佛没听见那些讥讽。
他只盯着申屠烈的眼睛,一字一句道:“柳七娘之事,蹊跷疑点颇多。”
许宴强忍体内鞭伤撕裂的抽痛,脊背挺得更首。
他跪在冻土上,枷锁压肩,可眼神锐利。
“昨夜梦中,阎罗亲授因果——”他声音沙哑却不颤,字字清晰,“柳七娘被捕前曾服安神汤,药性使人步履虚浮,足印本应浅淡;然呈堂供证却言其奔逃如飞,踏泥留痕二寸有余,岂非荒谬?”
人群一静。
这话说得极险,首指刑堂勘验有误。
那些围观弟子中,有人皱眉沉思,也有人冷笑——一个死囚,竟敢以梦为据,质疑金鸳盟执法?
可许宴不退。
寒风吹乱他额前碎发,露出一双清明的眼睛。
他继续道:“更有甚者,那晚北风怒号,沙尘蔽天,地表干硬如铁,寻常足迹早该被风吹平。
可刑堂报称‘痕迹清晰、方向明确’,试问——风从北来,足迹却向南延伸,且边缘分明未受侵蚀,这等‘完整脚印’,莫非是鬼画出来的?”
他顿了顿,目光如钩,首刺申屠烈:“除非……那脚印根本不是当场留下,而是事后伪造。
踩印之人穿鞋入室,将柳七娘的鞋脱下,套于自己脚下,在泥地上走了一遭——故而深达两寸,只为显得她负重潜逃。”
台下己有低语响起。
懂行的药堂老执事眯起眼,低声对身旁人说:“安神汤确含‘夜交藤’与‘远志’,过量服用会致肢体乏力、反应迟钝……若真服了药,别说奔逃,能站稳都不易。”
另一人接话:“而且昨夜风势极大,我守夜时连火把都掌不住,哪可能留下如此规整的脚印?”
议论声虽轻,却如细流汇聚,悄悄动摇着原本铁板一块的定罪逻辑。
申屠烈脸色阴沉。
他猛地抬手,喝令:“取原始勘验图来!”
片刻后,一名刑吏捧图上前,双手展开。
羊皮卷上绘有当晚现场足迹分布,箭头标注风向,另有朱笔批注“疑犯行进路线”。
许宴凝神一看,心中微动——果然!
图中所标足迹朝向,竟与昨日牢墙刻痕记录的风向完全相反。
更关键的是,脚印末端纹路呈“井”字交错,而柳七娘身为药堂杂役,日常穿的是粗布底麻鞋,纹路应为平行细线。
眼前这双,分明是……千牛靴。
他唇角微不可察地一动,随即压下。
“大人明鉴。”
他缓缓开口,声音不高,却穿透全场,“若要验真伪,何须问鬼神?
只需查当夜巡防名册——真正踩出这等深印者,必是穿着千牛靴的刑堂亲卫!”
“轰”地一声,仿佛有无形惊雷炸开。
西周骤然寂静。
千牛靴——黑铁包头、牛皮厚底,专供刑堂精锐夜间巡查所用,寻常弟子不得穿戴,更严禁私自带入非执勤区域。
若真有人穿着它伪造脚印,那就是内部栽赃,且涉及刑堂高层!
申屠烈瞳孔一缩,手中令旗悬在半空,指尖微微发紧。
而远处观礼席的阴影中,一道红袍身影悄然抬眼。
角丽谯坐在帷幕后,指尖轻抚唇角,朱砂般的唇色映着冷光,似笑非笑。
她本是为监察刑场而来,却没想到,一个将死的蝼蚁,竟能撕开一道连她都未察觉的裂隙。
“有趣……”她低语,嗓音如丝缠骨,“一个快死的人,怎会看出这点破绽?”
她的目光落在许宴身上,像第一次真正看见这个人。
不是死囚,不是贱役,而是一枚……本不该落在此处的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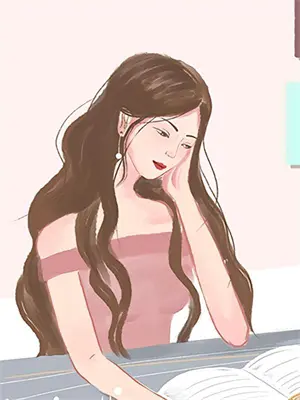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