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租界边缘的枪声像年久失修的座钟,每隔半小时就要在暮色里磕绊几下。
余鸢摘下听诊器时,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抖落二月霜。
圣玛丽安教会医院三楼的玻璃窗上,还嵌着三天前流弹留下的蛛网状裂痕。
"磺胺粉告急,玛尔大修女说只能优先给军官使用。
"护士小林捧着搪瓷托盘的手指在发抖,纱布边缘渗出的血渍己经发黑。
走廊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士兵突然爆发出剧烈咳嗽,浓痰混着血沫喷溅在米色墙裙上。
余鸢用手术剪剪开第十九个伤员的绷带,腐肉的气味让她喉头发紧。
十九路军撤退时留下的这些年轻躯体,大多带着被达姆弹撕开的创口。
她至今记得三天前的深夜,值夜的陈医生在手术台前突然瘫倒在地——那个十六岁小战士的肠子流了满地,而他自己的白大褂下摆还在滴着脑浆。
"余医生!
"护士长玛尔大修女突然撞开手术室的门,银十字架在她灰白的鬓角间晃动,"中央军的人要征用手术室!
"她浓重的比利时口音裹挟着恐惧,就像她袍角沾着的血渍般挥之不去。
六个持枪士兵踏着军靴冲进来时,余鸢正用骨钳夹住嵌在胫骨里的弹片。
领头的中尉用枪托砸翻了器械推车,镊子与手术刀叮叮当当洒了满地。
"让开!
"中尉的刺刀在无影灯下泛着蓝光。
余鸢抬头望去,担架上深褐色的将校呢军装己被血浸成紫黑,男人右手握着的勃朗宁手枪枪管还在冒烟。
走廊里突然响起惨叫声——某个试图阻拦的伤员被刺刀捅穿了手掌。
余鸢的口罩微微起伏:"这里是教会医院,不是战场。
"她继续转动骨钳,伤员小腿突然喷出的血柱染红了她的护目镜。
中尉的枪口顶住她后颈时,她听见担架上传来金属碰撞的轻响。
"要么现在给我取子弹,"男人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生铁,"要么我让这些杂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战场。
"他左手按着的肋下伤口正在汩汩冒血,肩章上的两颗金星却亮得刺眼。
手术室突然陷入诡异的寂静,只有男人腕间的欧米茄怀表在嗒嗒作响。
余鸢转身时,正撞进一双鹰隼般的眼睛——那瞳孔深处跳动的不是疼痛,而是某种困兽般的亢奋。
当她扯开被血黏住的军装时,三道蜈蚣状的旧疤赫然横亘在胸肌之间,最新那道刀伤距离心脏仅差半寸。
"磺胺粉。
"余鸢话音未落,男人突然抓住她的手腕。
他虎口的老茧刮得她生疼,掌心的温度却烫得惊人。
"先给我打吗啡。
"他扯动的嘴角牵动锁骨下方的烙印,褪色的囚犯编号在无影灯下泛着青灰。
走廊突然爆发的日语嘶吼让所有人僵在原地。
余鸢的柳叶刀悬在弹孔上方时,手术室的门被霰弹枪轰成碎片。
戴圆框眼镜的日本军官踱步而入,黑牛皮军靴踩在玻璃碴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。
"贺司令,您像受伤的狐狸一样逃进租界的样子真可怜。
"军官的汉语带着京都腔的粘腻,他身后的士兵正在给南部式手枪装弹。
余鸢感觉到手术刀柄己被冷汗浸透——三天前在停尸间,她见过被这种8毫米子弹掀飞头盖骨的尸体。
贺隋突然低笑起来,震得伤口又涌出股股鲜血。
他沾血的手指划过余鸢的白大褂下摆,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,突然将她扯进怀里。
"亲爱的,现在可以给我打吗啡了吗?
"温热的鼻息喷在她耳后,勃朗宁手枪却悄悄顶住了她的后腰。
日本军官的镜片闪过寒光:"这位医生小姐,不如我们做个交易?
"他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抚过手术台,"告诉我这位司令把密码本藏在哪里,我保证你和你的医院......"话音未落,贺隋突然扣动扳机。
子弹穿透日本军官的右肩时,余鸢被他拽着滚进器械柜后的死角。
爆裂的枪声中,她看见玛尔大修女胸前的十字架炸成碎片,中尉的肠子挂在无影灯上晃荡。
贺隋的手指在她腰间摸索时,她才发现自己的白大褂暗袋里不知何时多了本牛皮封面的小册子。
"别眨眼。
"贺隋在她耳边呢喃,突然暴起将手术刀掷向电闸。
黑暗降临的瞬间,他滚烫的唇擦过她的耳垂,"天亮后去霞飞路32号找钟表匠,说怀表要换发条。
"当租界巡捕房的哨音响起时,余鸢在满地血泊中摸到了贺隋留下的鎏金怀表。
表盖内侧用血迹画着诡异的符号,而手术台下的阴影里,日本军官被割开的喉管正汩汩地冒着血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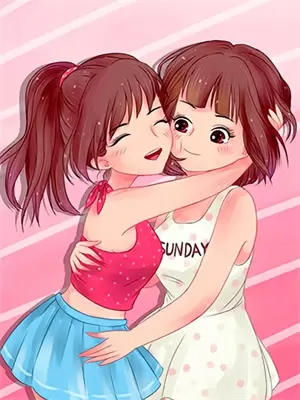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